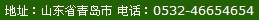|
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善行天下 http://m.39.net/baidianfeng/a_6359028.html ▲纪录片《四个春天》剧照 没看《四个春天》之前,赵珣曾在一年时间里,亲历了身边6个生命的离去。“一个人面对这么大的死亡密度是很可怕的。”这位导演兼编剧说,那时,她很想抚慰这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庭。 正巧在豆瓣同城上,网友“起床.吃饭”发起了其纪录片初女作的试映会。放映时间年1月20日,在北京朝阳门附近的27院儿里举行,片名叫《四个春天》。 放映前,赵珣在人群里一眼认准了一个圆脸的男子,脸上透着中年人的干练和几分小孩的率真。她径直走向了他,两人相视片刻,略显尴尬地,试探性地叫出了彼此的网名。 “我称他‘饭叔’。”赵珣说,五六年前,他们就在豆瓣上认识了,但从没见过面,也没看过他的个照。“饭叔”真正引起她注意的,是他年在豆瓣上发表的相册“回家”系列。从那多张照片里,她发现了“很不一样的东西”,“比如父母互相喂食,一起看书的照片,神情开心自如。大多数人面对相机多会紧张或摆拍,可这些照片里的景与人完全融为了一体。” ▲“饭叔”发布在豆瓣相册里的照片 《四个春天》开场不久,赵珣就对它的品质有了一个基础判断——“这部片子我可以帮他推上院线,至少可以帮他做完我能做的事。”放映完后,她再次找到“饭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同意,我们回家就做准备。” “好啊,那就做呗。” 她记得那天,两人都“没打一点弯”。离开时,《四个春天》的海报还在外张贴着,上面印着“饭叔”的真名——陆庆屹。 ▲陆庆屹近照受访者供图 三天后,赵珣与她的先生——制片人王立学将陆庆屹请到了家中。那天,他们聊了近8小时。陆庆屹记得,大部分时间都是这对夫妇在听他讲述父母、哥哥姐姐和他的故事。 1 “一辈子不让你受委屈” 在黔南,莽莽群山中塌陷出一块矿地,地势东高西低,有些褶皱,依势而建的屋宇错落有致。登高远望,青山如浪,起伏间一座孤岛般的小城,就是独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家在广西罗甸,刚从贵州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学生陆运坤被分配到这座贵州最南端的小城教书。黑白照中,他的眼神青涩专注,头发乌黑蓬松。在陆庆屹的笔下,当时的陆运坤是个“传奇“——“父亲从大学起,自学了很多种乐器,我细数了下,有十多二十种吧,吹拉弹唱无一不通,但也因此无一精通。在西南山区的小镇里,他也算是个传奇了。” ▲《四个春天》剧照 “那时候的大学生很穷。”陆庆屹问李桂贤,当初,你到底看中了爸的什么?李桂贤就是不说。再多问,她只回答,“看到你爸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人挺好的。” 在与陆运坤的结婚照里,抢眼的是李桂贤从外套翻出的白色衣领和一双大眼睛里藏不住的倔强与爽朗。“母亲唱花灯很传神,花灯是一种用方言演唱表演的地方戏,这种舞台戏对眼神、表情和身体的表达能力要求较高,以嬉笑逗乐为主,每每演出,台下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陆庆屹说,母亲年轻时是整个家族的顶梁柱,能歌善舞又做得一手针线活,身边不乏追求者,其中就有父亲——“妈的妹妹是爸的学生,爸就拜托她给妈偷偷捎信。” ▲陆庆屹父母的结婚照受访者供图 相恋后,李桂贤带着陆运坤去见自己的父亲。父亲说,陆老师挺好,就是太瘦了。那个年代,“太瘦”意味着不能挑起生活的重担。陆运坤知道后,郑重地向李桂贤表态,“你放心,我保证一辈子不让你受委屈。” 就这样,他们在用报纸装点,摆放了几件旧家具的屋里举行了婚礼。为了那顿客人只是带米来庆贺的婚宴,两人稀稀拉拉还债还了好多年。 年年底,陆运坤与妻子带着一对儿女——陆庆屹的哥哥姐姐从独山到了麻尾。4年后,陆庆屹就出生在了这座被苗族与布依族山寨环绕的小镇上。 童年记忆里,姐姐从麻尾考到了省重点中学,中央民大的招生老师也是在这里挖走了年仅十岁,乐感好又不怯场的哥哥,将他带去了北京。 “我妈说:‘把你们三个养大,说辛苦也好玩。只要我看见别家小娃有什么穿的吃的,就会想办法给你们搞来。有钱就买,没钱买就自己做,不会做就偷偷学。反正我就不希望你们羡慕别人,我才不要你们在物质上低头做人。’”陆庆屹转述母亲的原话说道。 ▲《四个春天》剧照 年,是一家人从麻尾搬回独山的第18年。负债累累,好不容易盖起的房屋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大半个家业尽毁。目睹此景,母亲第一反应是冲进废墟,寻找那些纪录全家人过去的老照片。而父亲则是在短暂的伤心之后,从灰烬里扒出了背板快烧成炭的小提琴,站在天台上吱吱哑哑地拉起。 陆庆屹写道,从墟烬里扒回的照片——“只残余了一个小木盒里的那些。让父母沉痛了许久,时常想起不禁长吁短叹。” 2 “想做中国最好的导演” “有一回,我梦见了‘起床.吃饭’。醒来觉得不错,恰好QQ号,豆瓣ID都需要起名,就用了它。”年1月25日,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餐厅里,陆庆屹顽皮地冲红星新闻特约记者说着。 8年,他有了第一部相机。起初,他的视野焦点是那些引起视觉触动的风物,是家乡的田园牧歌,是捕捉父母的点点滴滴。年,他在豆瓣上相继发表了《我爸》《我妈》两篇短文,受到不少网友的推崇点赞后,他决定用视频代替摄影纪录父母的世界。更加促使他想将素材剪辑成片,以此作为献给父母的礼物的是年大姐陆庆伟因患肺癌突然病故。 提起大姐,陆庆屹清楚地记得,15岁那年,他因为在学校受了委屈,背上书包,义无反顾地爬上了离开独山的火车。“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去。” ▲陆庆屹旧照受访者供图 他首先想到的是,投奔已在沈阳工作的大姐,他从小就和开朗活泼的大姐最为亲昵。为了防止他再度逃跑,大姐把他锁在了家里,直到母亲出现。母亲带来了他的行李,直截了当地说,独山你肯定是回不去了。 “我很清楚,我在独山没有任何前途。”陆庆屹说。但紧接的现实是,大姐快要结婚了,他又何去何从? “我去沈阳,将他带到了北京。”1月22日,在北京朝阳路的一家咖啡馆里,陆庆松平静地说道。那时,他还在清华大学任音乐教师,在校园8号楼有一间宿舍。他把陆庆屹接来同住,让这个率性而为的弟弟过上一种不去上课,也能读书、画画与踢球的“校园生活”。 期间,陆庆屹想过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他参加省队的专业培训,因腿受伤导致了梦想的破灭。此后两年,他居无定所。没有学历没有技能,找工作接连碰壁。因交不出房租,他睡过公园的硬板凳;因被朋友的父母嫌弃,他不得不到深夜才敢翻进朋友为他敞开的窗户,进屋借宿……没钱回家,却也不想仓惶狼狈地回家。直到年,他在一家出版公司获得了一份编辑工作,生活的压力才得以暂时缓解。 “当年在清华,我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那一年,他快要毕业了,邀请我跟他一起到他的家乡湖南去玩。他为我买了火车票,我也答应了。但在启程前一天,没有任何理由地,我突然想,我为什么要接受他给我买的票?”陆庆屹说,那时,他能接受一个特别贫穷的朋友为他买一顿饭,却不能接受一个富有的朋友为他买一张票。 “拒绝了以后,我和他见过一面,就再也没有见过了。”陆庆屹听说,好友毕业后,进了一家大公司做上了高管。他笑了笑,“按别人的说法,我放弃了个极好的机会。在我最困难时期,如果我俩还是好朋友,他应该会帮我。但我觉得,我的决定也是改变我人生的一个机会。” 年,厌倦了整天看别人稿件,想寻找自己创作方向的陆庆屹,辞去了出版公司的工作。做了短时间的酒吧歌手后,他跑到广西罗甸县罗捆乡的矿山去采矿。 ▲陆庆屹做驻唱歌手时的旧照受访者供图 “黑暗中,石壁上炸开了一个十几厘米的小口,里面是一窝晶莹的水晶,一根根指向圆心……一瞬间我被一股感动的浪潮席卷了。这种世间的极品,埋藏在山体里,没有人知晓,而它们仍然朝着最纯净最完美的方向生长。我突然明白,如果没有自我净化的决心,一直渴望的个人’自由’,乃至在生活中艺术化的自我放逐,不过是无聊的自悲自怜,是逃避为人责任的借口。”自那之后,陆庆屹离开矿山,回到了北京。 “自己一直没有放弃思考与对人生的探索,不管活成什么样,起码内心不愿浑浑噩噩。”陆庆松说。 年春节,陆庆屹在独山参加了高中同学的聚会。KTV包房里,一帮中年人在彩色的闪灯下纵酒放歌,他却坐在沙发抽烟发呆。同学问他在想什么,他说他在想未来。他们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他说,我有,我想做中国最好的导演。 3 从上百小时的素材到院线版的剪辑 “看到父亲的衰老如此之快,我意识到必须开始剪辑了。”陆庆屹在书中写道。 年,他看到了一篇对导演侯孝贤的访谈。有电影学院的学生向侯孝贤请教,虽然在学导演,却不知道怎么开始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对方回答道:想拍就去拍,你不去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 这句话在他的心里引起了震动。 “但是我不懂剪辑。有一个星期,望着个小时的素材,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陆庆屹嘲笑自己,后来还是抱着电脑到中关村安装剪辑软件时,店里的小哥提示他,不会使用就买书学嘛。他才恍然大悟,买了两本书关起门来琢磨。 刘耀华与陆庆屹是在京相识多年的好友,后来又与他住在同一村里。他是一位做观念艺术的艺术家,“最早讨论时,我说过,他本身作为家庭成员去拍摄,情感就已经内含在了镜头里面。后期剪辑时,不要想着去突出情感,否则很容易变得矫情或是让人感到刻意煽情。”刘耀华说。 陆庆屹说,粗剪版有五个半钟头。“他认为里面的素材拍得都很好。我说,你得把它作为一部放给观众看的片子去看。那些在美学与功能上有重复的内容,就得舍弃。”刘耀华对陆庆屹提出了意见。他们把自己当成普通观众反复去感受,又反复去修改。半年多后,他们终于剪出了一个两小时的版本,拿到尤伦斯作第一次试映。 这也是赵珣在第二次试映上看到的版本。 “声音上的困难非常大。”赵珣回想起将《四个春天》打磨成院线版的过程时说道,比如说导演录下的脚步声是不够响亮的,但在这个环境里,我必须要有脚步声,必须要还原这一声音;还有爸爸扛着一棵小树,然后走着走着走到泥地里,我们要找合适的脚步声贴上……如果不做的话,普通观众坐在影院里看那些画面,就不会觉得它们的美。所以,我们做了大半年,几乎做了每一场戏每一个环境的声音还原。 “整个片子的气息应该是空,远,高。而且,不是那种很冷的‘空’。”陆庆松为《四个春天》作了曲。片中最打动他的是,父母走在田垄上,母亲唱起了《花儿与少年》,她边唱边俏皮地冲父亲回眸一笑,宛如回到了初恋。“在家也常见他们一唱一和,可通过镜头提纯出来,就觉得格外美。” ▲《四个春天》剧照 曲子舒缓地在片尾流动,父母在姐的坟前歌唱,微风拂过远山绿田与潺潺溪水,那是《论语》中对宁静致远的向往:风乎舞雩,咏而归。 4 “我想表达的东西,我不会说出来” 年,分钟的《四个春天》在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获“最佳纪录片”。 “我觉得他一点变化都没有。”赵珣记得,他们一行去武汉参加华语影像论坛时,陆庆屹一看见长江就把他们抛在身后,自顾自地往江边跑,兴奋地拿起手机拍个不停。艺术总监问他,你第一次来武汉?他说不是,很多年前就来过。 在她眼里,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干电影的人,“经历丰富又难得地保持着对事物的童心。” “如果不干别的,画画也绝对会有成就。”迄今为止,陆庆松都对陆庆屹的绘画天赋毫不怀疑。当年在清华,他请朋友指点弟弟的绘画。朋友随口言道,那你画我吧。陆庆屹画完,朋友看后说,还用教什么?你画得比我都好。“线条,轮廓,还有人物的状态都把握得非常准。还有,他的画没有匠气。”哥哥陆庆松回忆道。 “那是我哥不懂画。”陆庆屹却说。据说当年,他凝视了画家米罗的一幅作品后,断然放弃了这条路,“我最敏感的是光感。光的强弱,光的软硬度,宽窄度。” 《四个春天》上映后,评论如水面泛起的涟漪般袭来。“我同意它不完全是田园牧歌式的东西。”赵珣说,有人能从片中反观到自己,她表示尊重,可她不想给这部片子加上更多沉重的意义,“我为什么想让那些失去亲人的朋友看这片子,我是想让他们得到放松。” 刘耀华却说,《四个春天》有“水里的刀子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老两口逢年过节才能盼回儿女?另外陆庆屹和他哥至今都是单身,姐姐的婚姻在片中显示,似乎也不幸福。而反观他们的父亲在饥饿难耐的时代,婚姻却是幸福的。我们今天的物质还不够富足?而我们的幸福又在哪里呢?所有的生离死别都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进行,只不过影像没有刻意强化这些。” “我当然有我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我不会说出来。”采访即将结束时,陆庆屹一脸认真地说道。 当晚,他走出三里屯街头。瞑色中霓虹闪烁,几个年轻人在街拍。他自言自语,为什么专盯着美女?清洁工也可以去拍啊。当走到地铁口时,他又轻声说,难道他们没有发现这种生活在消逝吗?我是在挽留。 (参考资料:《四个春天》陆庆屹/著-01-01南海出版社出版) 红星新闻特约记者丨白素北京报道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13801256026.com/pgzl/pgzl/3329.html |
当前位置: 罗甸县 >四个春天导演我不会说它要表达的是什么
时间:2023/1/3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畅通农村水网最后一公里
- 下一篇文章: 福泉聆听劳模故事感受劳模力量弘扬工匠精神